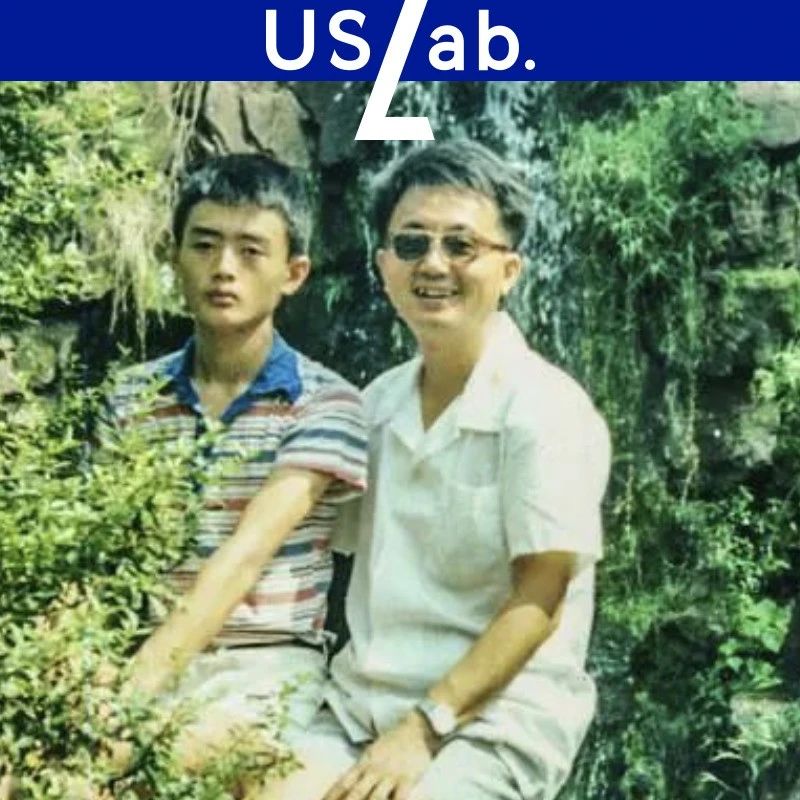Skip to content
2022年初,我们曾报道了天才译者金晓宇的故事(戳:男子从殡仪馆打来电话:能不能写写我们的天才儿子),当时的他已经进入中年身处。来访者将他过往的经历来来回回问过许多遍:右眼因为童年的一场以外视物困难,大学第一个学期的寒假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,试图自杀失败后被父母养在家里,人生轨迹与大多数人产生了偏移。事实上,那些对他来说都不再重要了。年轻时候的痛苦和青春本身一起过去了,他不断强调,自己已经50岁了——人生无从逆转,不可更改。为期、读书、游戏、翻译,金晓宇在这些事情上面度过了漫长的时间。过去十年,他在家完成英、日、德多语言共计17本书的翻译。至于社会标准里的那些,毕业、结婚、买房,他说自己达不到要求,也不想重来。如今,他只想着如何让生活延续下去,如何度过这个月,下个月,下下个月。如何与自己的病情保持平衡关系,如何在无数次觉得走投无路的状态里回过神来。
“一棵树上能开很多花,有的花会结果,有的花不结果,它就是人生。”
金晓宇君,你好。这几天你受到了太多的关注,一定不胜其扰吧。我在这个时候给你写信,好像时机不太对。但我们原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,完全没有任何交集。要不是你骤然出名,我又怎会知道你的存在呢?我设想了很多....如果异地恋,你能来我的城市看我吗?如果不能,那我多久去一次杭州呢?
金晓宇君,我幻想被突如其来的爱情击中,我坚定地选择了你,你也坚定地选择了我,然后就像《美丽心灵》的男主所说的,你就是我存在的原因……假如你爱我,双向情感障碍算什么,你抑郁的时候,我就当你是因我抑郁,你躁狂的时候我就当你是为我发狂。我会把你所有的症状都解释为你爱我。当你正常的时候,我们就老夫老妻。当你不正常的时候,我们就疯狂的恋爱。
这天下午,金晓宇终于从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脱出身来,窝回到自己十来平米的小房间,坐在老旧书桌前,打开电脑处理积攒的未读邮件。近几年,除了已经摘除晶体、视物困难的右眼,他的左眼视力也在下降,无论是看显示屏还是看字典和实体书做翻译,时间久了眼睛会泛酸。为此,他把浏览器的页面显示比例放大到155%。打开邮箱后,他拜托我把邮件念给他听。
几封未读消息躺在列表里,分别来自媒体(约访)、出版社(约稿)和《杭州日报》的副刊编辑。她在邮件里告诉晓宇,有读者给他寄来了电子邮件(发到编辑的邮箱),准确说是一封情书。晓宇坐在窗户旁边的椅子上,听到这里,身体坐直了些,笑着说,“让她发过来,大家欣赏欣赏。”他说这是自己这辈子收到的第一封情书——准确说有六封。来自一位40多岁的离异妈妈。对方在信中说,自己经济独立、财务自由,只是被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稿件打动,想要和晓宇进入一段婚姻。当然,如果担心自己觊觎财产,可以做婚前财产公证,或者只谈恋爱不结婚。在第四封信里,她又说,觉得晓宇目前最缺的是一个助理,她可以以交完社保后3000-5000的工资应聘。父亲金性勇走进来,听了个大概,根据他86岁的人生经验判断,这位女士大概率是来骗钱的,他“不反对他们交朋友,但是要慢慢地来,一步一步走”,“一定要互相了解的时间长一点,不喜欢贸然,这个东西容易出问题”。至于收到情书的感受,金晓宇说,“50多岁了还有什么感觉?没感觉了”。他沉默一下,重复说:“我都50岁了,马上就50岁了。”追溯这种“感觉”需要往前倒数许多年,他20岁出头,从浙江树人学院肄业后,有段时间被妈妈介绍到杭州教育书店工作。在那里,他碰见过同样年轻的漂亮女孩儿,同事阿姨鼓励他勇敢去追,但他坚持认为只有有钱才可以追女生,“喝个奶茶都要钱”,他说,当时自己的工资全都上交给妈妈,连那个钱都拿不出来,最终也没告白,更没写过情书。事实上,那时候他正陷入生活的泥沼,动弹不得。大学第一个学期寒假,他在南京一家医院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。退学后,父母担心他彻底和社会脱节,推着他出去工作。在书店做售货员,他经常觉得时间漫长得难以打发,甚至不如去做纯体力劳动的搬运工。到了现在的年纪,他对很多事情都看淡了,处世哲学变成:“把自己保护好了谁都是好人”和“(生活的)关键是工作、赚钱,然后能赚会花这样就行了。”自己赚的钱,最开始交给妈妈,现在放在爸爸那里,平时他只拿很少一部分,放在门口柜子上的铁盒里,用来买菜。很多人夸他显得年轻,完全不像已经50岁的人,但金晓宇能清楚感受到自己老去的踪迹。最先显露马脚的是体力,以前他能从家一路跑去之江饭店再一路跑回来,现在没跑多远就开始呼吸短促。还有虽不明显但必然生长出来的白发、越发浑浊的眼白、黯淡下去的眼神。2021年12月23日,他出院回家,快进家门时,爸爸才告诉他:妈妈不在了。等他去殡仪馆时,妈妈已经是很多小格子里的一个了。他蹲在那里很久,直到爸爸说,好了,我们走吧。他说,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如今只剩下爸爸一个了。如果没有束缚,随他的便,自己早就出去旅游了。也不知具体要去哪里,可以随便带本书出门,最好是日文的、薄薄一本,在外面看完了回来再翻译。年轻一些时,父母极力将他往外推,他将自己关在家里,如今反而想要出去走走。但他现在走不开了。金性勇86岁,腿脚不便,走路只能一步一步往前慢慢挪,晓宇和他一起出门,一般到小区外的公园,或者运河边,再远的话他怕父亲身体支撑不住了。我待在自己的房间里,坐在窗边的桌子前,手托着腮,就像往昔那样。是啊,在此时的我看来,那些都已成往昔了。
从1988年至今,金晓宇在这栋老房子里度过了漫长的34年。家具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式,洗菜的水池同样用来洗脸,昏暗狭小的房间里有股陈腐的气味。直到表姐用扫帚从卧室的天花板上扫下来三处蛛网,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曾和蜘蛛共处。某种意义上,与同时代的人相比,金晓宇的时间仿佛是凝固的。他以一种古典而自在的方式活在过去:他不知道时下最流行的那两款短视频APP。他从不打车,心情烦躁的时候出门溜达,就随机选一辆公交车,绕一圈再回去。偶尔,他会察觉到一些变化:十年以前,晓宇在一家叫做国美的实体店买过电脑显示屏,前几天他再去那儿,想换台主机,发现店里早就不卖台式电脑了,改卖汽车和家庭影院了,“弄不好可能还有3D的”。他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主要是听广播。以前听收音机,后来在手机上下载了央广网APP。他没有这个时代人们信息过载的焦虑,获取信息几乎全靠偶然——听的时候在播什么新闻,他就了解到什么。比如他知道双减,但那天的简讯没展开,他至今不知道这个政策具体指什么。他听过猿辅导的名字,以前天天打广告,却对它最近的变动一无所知。他让我帮忙在淘宝上下单一个CD播放器,想先在家自学西班牙语发音,如果再住进精神病院,就可以直接带书进去看了,电子类产品是不能带进病房的。但在另一种层面,他的生命体验又极为开阔:因循要翻译的外文小说与传记书籍,他看过多部日剧,为了准确译出一些细节,他找来相扑比赛的视频。《嘻哈这门生意》书里涉及几百首嘻哈歌曲,那段时间,家里没完没了地播放音乐。塔可夫斯基的每部电影他都至少看过两遍,有些细节场景会反复观看。由他翻译的书籍被邮寄到各路读者的书桌前,触动着遥远的心灵。高中历史老师小希是在班维尔的《诱惑者》那里结识金晓宇的。班维尔是爱尔兰最著名的作家之一,作品以表现生命的悲剧性以及存在的虚无性为主题。与众不同的叙述风格意味着翻译难度在提高,而金晓宇翻译的版本全文流畅,将人物的内心冲突更直接暴露在读者面前。小希认为,与其他翻译者相比(如王睿、陆剑、戴从容等人),金晓宇的语言更加冷淡、直白,赤裸裸且带有锋芒。她猜测“一个能翻译出《诱惑者》的人,他的内心世界一定是丰富的,拥有对世界强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,有对未知的渴求以及对社会的思考”。在网络上看到金晓宇的新闻后,小希再去回忆《诱惑者》,觉得故事的主角斯旺与金晓宇的人生彼此暗合。斯旺极具数学天赋,想通过数字本身探索世界与生活的模式,最终发现那只是一场幻梦。斯旺在英文中指的是“天鹅”,他放弃了自己的身份,从天鹅变成了鹅。“他们面对这个世界时,身上的某些东西丧失了,只能每天重塑着自我,用零碎的记忆、感觉拼凑出一个新的自我。”她想,谁又会是金晓宇的“诱惑者”呢?是菲费利克斯(故事中一位长着狐狸似的脸的狡猾男青年,引导斯旺去做各种事情)亦或者是他内心世界的自我?但金晓宇说,关于内心的部分,是可以不与人交流的,承受就好了。“我总是把感情放在心里,有时候自己想一想,不表达。”因为疾病,他在社区里是被特殊关注的人,2009年,晓宇被鉴定为精神二级残疾。除了扔垃圾、买菜,晓宇很少出门。待在家里让他感受到自由,不用去上学和工作,也不用在意别人在说些什么。邻居龙哥以前常看到他的灯亮到深夜,直到看见新闻,才知道他是位译者,或许是在做翻译吧。2021年10月,金晓宇再一次住院,那时他的母亲曹美藻躺在病床上已经完全无法行动,也不能讲话了,父亲金性勇除了帮妻子喂饭、翻身,漫长的时间最多依靠三张报纸打发。这天,金性勇看到《杭州日报》的副刊「倾听·人生」栏目,忽然很想把儿子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。照顾妻子的间隙,他开始写一封长信,分三个部分写下儿子的过往、英译、日译的经验,最后把五六张稿纸寄往报社。等来回音时,妻子已经不在了,靠门的床空空荡荡,他把自己重新填了进去。但儿子金晓宇的故事借由网络传播,获得公众山呼海啸一样的回应。这个沉寂许久的家,忽然被拽入了热闹的新世界。金性勇几乎不拒绝任何突如其来的到访,老年手机这几天总是响个不停。他的耳朵不太灵敏,把老式键盘机的声音开到最大。多年没联系的老家亲戚打来电话慰问,从未合作过的出版社看到网络上的新闻想要请晓宇翻译新书,几家影视公司的影视改编权竞争已经进入焦灼期,背着双肩包、蓄一撮胡子的男制片人率先从北京飞到杭州,把合同摆在了老爷子面前。社区书记带着志愿者们到家里来给金性勇免费理发,五六个人挤进小房间,快门、手机拍个不停。领导、更大的领导都来了,慰问父子两人的生活现状。做适老化改造的师傅赶来金家巡检厕所,策划方案,准备年后动工。金晓宇的生活也被扰动了,不断与不同的人群合影,一回,他本来想挨着父亲站,被热情地拉到了画面的最中间。他也不拒绝,面色平淡。社区把所有媒体集中起来采访,在老年活动中心安排了圆桌,父亲、晓宇、社区书记、民警围坐在一起,底下乌泱泱一群记者和摄像机。问题一个个抛过来,父亲金性勇被晓宇推出来做“发言”,他自己坐在那里,头微微低垂,沉默着像个孩童。▎绳索
妻子曹美藻去世后,金性勇的时间突然悬置了下来,晚上睡不着,他开始吃起安眠药。在此之前的五六年里,他习惯了作为这个家庭的照料者,日常生活的艰难由他承受着,每天忙着做饭、洗碗、收拾房间。有时晓宇嫌他动静太大,会发脾气,他就赶紧回应,好好,我慢一点。“我��乖的”,他笑着说。他是晓宇的最佳翻译助手,帮他打印资料、纠错,最后用扫描仪扫描出来装订成本,再以金晓宇的名义寄到出版社去。出版社的编辑们并不知道,很多次的沟通都是由这位老人代替完成的。金性勇说,除了零星两个人,其他编辑都不知道晓宇的病情。社区书记觉得在这个家庭里,金性勇是最苦的那个,如果换成旁人,遇到这种状况大概早就疯掉了。她记得,曹美藻生病越严重的时候,老爷子越会跟他们说,自己一定要坚持,如果他不坚持了那么整个家就没有了。书记说,只要老爷子自己能做的事情,从来不接受任何帮助,“有老知识分子的骄傲在那里”。大部分情况下,只有晓宇发病,他才会主动求助社区,“老先生有他的纠结,他舍不得晓宇去医院,但那个状况他又控制不了”。之前,晓宇发病时,掰断过别人汽车的后视镜,快递员骑车经过,他将对方推倒,踢了一脚,对方断掉了牙齿。金性勇每次都是兜底的那个人:对不住,我儿子他有病,需要多少钱我赔给你。他对待晓宇的方式更像是对待小孩子。家里的客人要走之前,他会告诉晓宇,去跟人家打个招呼,告个别。吃完午饭的间隙,他会问,晓宇今天开不开心?对金性勇来说,看护好儿子已经成为生活的最大意义。曹美藻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后,早就忘记了他。金性勇记得,起初妻子还能动,每次吃完饭,他会和她并排坐在沙发上,拉着妻子的胳膊去打自己的手,这样可以加速血液循环。妻子每次都咯咯得笑起来。“她不认识我,她也不会说话,她笑的时候我就高兴。”晓宇说自己对妈妈的了解并不太多,只是觉得她太要强了。曹美藻是民盟成员,经常参加会议、组织聚餐。退休后她也从不闲在家里,每天早上9点准时到证券交易所炒股票,她有理工科缜密的思维,喜欢钻研规律,是附近老年人炒股团里的名人。她对生活非常热情,没得病的时候,晓宇和父亲的毛衣、裤子、鞋子很多都是曹美藻自己做的。晓宇觉得妈妈患病之后,对自己的控制力减弱,他形容这种状态是“无能为力”,并且坚信如果妈妈有的选,一定会管自己到底的。我们到访的这几天里,他许多次尝试理清自己对妈妈的复杂情绪。妈妈对他很有一套方法的,金晓宇说。你得听她的,如果展露迟疑,她会说动老师、同学来劝服你。她也会语言鼓励你,真金不怕火炼,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她帮你做一些决定,转学、参加成人自考、读最流行的国际贸易专业、学习语言、做翻译——金晓宇过去人生的关键选择,几乎都与妈妈有关。他说自己在家里选择服从。围棋是他少数的主动选择,近乎于孤注一掷。高中躲在家里不去念书的时候,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看围棋书。起初只是研读,后来他开始摆谱,执黑亦执白。他经常去买当时围棋界的专业杂志,大开本的《围棋天地》和上海那边出版的小开本《围棋》月刊(后来更名为《新民围棋》,于2002年冬季停刊)。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围棋,他在现实中找个对手都不容易,只能和同学或者邻居下棋,后来,他干脆跑到棋室里面跟赌徒对弈。他看到有篇关于自己的文章里写,翻译之于他是“生命中黑暗里的绳索”,其实不是的,他说,围棋才是,“只不过是个爬不上去的绳索,竞争太激烈了。”他在杭州棋院考到过业余二段,但最后也没能拿到职业定段赛的报名资格。金晓宇至今留有遗憾,觉得父母受“破四旧”的影响,不支持他走这条路。哪怕职业的路径没走成,他也一直还在下围棋。独自摆谱,研究死活题。直到2010年开始做翻译,再加上视力下降,金晓宇才慢慢不再下棋了。之后的许多路,都只是谋生,他开始听从妈妈的建议,学习外语,英语 、日语、德语,在上面花了接近10年的时间,才等来翻译的机会。翻译这条路最初是妈妈帮忙选的,但最后晓宇自己越走越坚定。他会把翻译一直做下去,这是他目前能把握的、最务实的活计。翻译为他与外部世界提供一种平衡状态:在家里就可以完成,不需要和外人打交道。他也没什么特别想要翻译的作家或者书籍,他想选最简单的,最好是日文作品,那个字体比英文大一些,比较好读。至于外界赋予这个故事的那些幻想,都被他一一戳破了。他说自己不是天才翻译家,只是刻苦想要描摹原作的画匠。在收到第一本翻译样书时,看到“金晓宇 译”的字样,他没觉得激动,只是欣慰,“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,还有爸爸妈妈的帮忙。”他觉得如果没有妈妈帮他走上这条路,自己更不知道做什么了。得病后,曹美藻对待生活松散许多,晓宇管她叫“老猫”,每天抱她下床,放上轮椅推到餐桌边。母亲喜欢吃蜂蜜蛋糕配牛奶当早餐,他经常去帮忙买。当他想像照顾小孩一样照顾妈妈时,她却没有知觉地离开了。晓宇非常自责,经常想,如果自己没去医院,待在家里看着她,老妈是不是没那么早走?金晓宇把母亲诊断、检查的节点记录下来,想等哥哥回来给他看。金晓天1998年去澳大利亚读MBA,如今已经在那里定居,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“24年了,快得很”。晓宇上次见到他,已经是7年前了,妈妈刚生病的时候,他回来过一次。这么多年,晓宇只收到过哥哥寄的一封信,一直留存到现在。那时候哥哥刚出国没多久,寄信来问候新年快乐,顺便向他介绍自己在澳洲的生活学习情况。当时金晓天的生活费需要靠自己打工挣来,他告诉晓宇自己正在做清洁工,为老板开垃圾车。晓宇说,后面哥哥在报社工作过,效益不好,倒闭了,如今在一家辅导机构做老师,辅导华人学生。金性勇对这个离家多年的大儿子态度疏离,他知道他过得也不是很好,挣一份工资要养活四口人。兄弟两个他一样疼爱,但他说,晓宇觉得父亲更喜欢哥哥,对自己是一种同情。金性勇戴一顶贝雷帽,如今是个小小的驼背老头,坐在沙发上讲起这件事,心里仍然觉得刺痛。“我说儿子,我疼自己的孩子,我爱他,你用的同情是我不接受的。”他非常严肃地跟晓宇说,这不是同情,我要帮助你,这是父亲的责任。我到访的时候,再过几天又是农历春节,晓宇还不知道要怎么过。中午,我们坐在餐桌边吃饭,他突然讲起这张餐桌的变化来:“以前有四个人,然后我哥哥出去以后有三个人,现在两个人”。妈妈还在的时候,他们三个人会聚在这里涮火锅。晓宇想起以前,那时候最好了,哥哥也在,爸爸还年轻,炒菜特别好吃,“讲究色香味形”,不像现在这样应付。逢年过节肯定是要做鳜鱼的,还有喜蛋,“把鸡蛋先煮熟了剥开切成两半,上面是肉夹馅,底下是鸡蛋”。▎不结果的花
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后,金晓宇几乎每年都会住进医院。很难说清躁狂状态来临的征兆,似乎面对生活中所有自己无法掌控的事件时,都是“坏时刻”到来的前奏。晓宇提到上次想买一双换季运动鞋,他先去了大卖场,又去了轻奢品店,最终也没有买回来适合的,这让他焦躁。他分析后来入院或许也受这次事件的影响。躁狂发作时并没有最开始传播的故事里所赋予的浪漫色彩。晓宇说,发病时砸东西,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,妈妈的缝纫机和爸爸买的电脑,之前发病他都差点砸下去,被爸爸拦住了。在医院里,他被四脚朝天绑在床上,最长的时候有十多天。这些年,疾病将他困锁其中。曾经的同龄人几乎都已成家立业,似乎只有他在某种层面上留在原地。媒体报道之后,有位姓韩的高中同学辗转联系过来,想让晓宇一起去看望高中老师。以前两个人同路,放学后经常骑车一起回家,在学校,两个人混在足球场,晓宇记得同学踢得很好,冲在前面,他却总在后面呆着。对方后来出国留学,如今已经是浙江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了。金晓宇记得上一次和他有交集,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。当时,同学从美国留学回来,正经历一段稳定的恋爱,他告诉金晓宇,自己快要结婚了。晓宇后来没有收到他婚礼的请帖,他猜测对方“可能知道我经济条件不好,是吧?”这天下午,韩同学打电话来,晓宇直接把手机递给了父亲。后来金性勇说,他感觉晓宇可能有自卑感,“像他们这个年纪可能事业有成的成家立业了,他自己这么一个情况,那么他不乐意,不乐意有什么办法?”但晓宇说,他并不在意这个,一棵树上开许多花,有的花结果,有的花不结果。他只是凑巧成为那朵不结果的花而已。他很早明白生命具有偶然性。小学升初中的那一年,金晓宇跟随父母的工作调动,从天津转学到杭州。这里的学生说方言,他听不懂,加入不了别人的谈话。杭州的冬天下大雪,同学们在打雪仗,他没参与,一个人在旁边滚了很大的雪球。那时他的左眼已经开始近视了,坐在教室的中间位置,他看不清楚老师黑板上写的公式,因为害怕戴眼镜被同学们骂成“四眼狗”,他没敢告诉家里,也没有告诉老师。直到有别的同学先戴上,他才去配了眼镜。他说自己信奉的道理是“枪打出头鸟”,不要跟别人不一样。后来我才明白他这句话是一种隔着漫长时间的“反思”或者“自嘲”。在当时可不是这样。那会儿他虽不是刺头,但面对很多事情总是不服,别的同学欺负他,他就反击回去。有记者问他,父亲说他一生都没有朋友,是不是真的?金晓宇说,如果顺其自然的话肯定会有朋友的。那能介绍一下你想到的一个朋友吗?金晓宇讲不上来,反复解释“顺其自然”和“人以群分”。后面有天,他突然向我讲起他的一位朋友,一位已经失去的、最好的朋友。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,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位高考复读班的同学,年纪比他稍大一些,“从来没有欺负过我”。对方后来考上了宁波大学日语系,大学毕业那年的暑假,他到杭州来找晓宇,邀请他到宁波玩儿,去自己的学校转一转。那时晓宇已经从树人大学肄业,确诊了躁郁症,和对方的人生差距越来越大。晓宇直接拒绝了,但朋友的盛情难却,“他说一定要去,一定要去”。在宁波,朋友非常自然地向晓宇介绍自己的经历,他在大学非常活跃,加入了团委、学生会。晓宇觉得很不舒服,认为对方有一种优越感。朋友不是刻意呈现,晓宇解释, 这种际遇悬殊本身就是一种优越,“是得意的,你是失意的。”回到杭州后,晓宇向朋友摊牌。“接我去宁波玩,吃饭、路费多少?我说,50块够不够?不够。100够不够?不够。150、160?我就这么加上去,直到他说,够了。我说(钱)够了我给你,你走人。”“他说我这么一走以后永远不会来了。我说你走吧,他就走了。”之后,两个人再也没有联系过。此后人生的湍流从未止息,这些细节仍然牢牢留在晓宇的记忆里。母亲去世后,晓宇重新整理家里的东西,翻到当年和朋友在宁波的合影,似乎重新回到了那个夏天。去年最后一次入院前,他独自一人前往温州。在此前的所有采访中,他解释的原因是,父亲照顾母亲很累,脾气急躁,他想出门透透气。这当然是事实,但是,从杭州可以延展到中国的数个乡镇与城市,为什么是温州呢?后来他说,那位朋友现在可能在温州公安局工作,之后他又解释,自己不是刻意要去找他,“我就去看一看温州,看看到底在什么地方”,“公安局的牌子我看到了,我通过派出所找的救助站,救助站给我买的火车票,我就自己回来了。”▎独立
一月底的某个早晨,我来到晓宇家时,金性勇正趴在桌子上填写一份申请表。晓宇背着手站在后面指导,像是监督小学生写作业的老师。两天前,浙江省翻译协会邀请晓宇入会。这解决了金性勇的一桩心事:晓宇终于有一起交流的人了,有组织有团体,翻译机会也会更多。金性勇86岁,思维的迟缓反映到写字速度上,一边念着一边落笔。写到作品一栏时,由于译著很多,表格填不下,金性勇写了几个英译中作品后,想要加一个“等”字,晓宇立刻声音大起来,“等什么等,我本来就没他们那个,全国翻译考试都没考,还不弄这个,还等一等,那我等到猴年去了!”填到期望参与活动一栏时,晓宇让他写“听从组织安排”,金性勇写成了“服从组织分配”。晓宇整个人快要炸裂了,他后退两步又走回来,几乎于咆哮着,“听从!怎么变服从了!改成他妈服服帖帖了,我跟你讲,我宁愿服从(的话)我肯定早就死掉了!我自由职业,我还服从他?你那时候包分配,谁给我分配工作了,我这么多年……我还服从他?!”填完表格后,金性勇坚持要立刻交到社区去。窗外的雨正下个没完没了,杭州冬天的冷湿漉绵密,逐渐渗入身体。金性勇撑着伞走出家门,金晓宇没有跟来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露出无奈、疲倦的神情,在之前的几天里,面对往来各方,他始终周到热情,笑眯眯地瞧着对方讲话。晓宇脾气急起来就是这样的,已经习惯了,他说,自己脾气也很固执,吵起来要跟他争几句道理。不能总是让着他,那样他就没办法准确理解对错。但每次,当感受到儿子情绪的细丝绷紧,激烈地快要断裂时,老人就败下阵来,“会想起来他有这个病”。这位父亲说,双相障碍是种“好讨厌”的病,他曾强烈地试图认识它。他去问过浙江二院的医生,医生说这个病很难讲,好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,犯病的时候你一点办法没有。在信息还没有那么流动和公开化的时期,金性勇会到武林门那里的医学情报研究所查资料,看精神疾病方面的专业期刊,那里有最前沿的汇编。如果在杭州的研究查不到相关杂志,他就和单位申请出差,到北京或者上海去,那里资源发达,肯定可以找到。比如北京协和医院,期刊就很全面。他把资料复印下来,一份留给自己,另一份会送给一位姓吴的医生。他跟这位医生商量,把晓宇用药的用量做个对照,如果可以减量,看看效果有没有变化。精神类药物有副作用,他想尽量让儿子少受影响。他现在的心事是,怎么能让晓宇独立呢?这些年把他养在家里,如果有天自己走了,晓宇要怎么办?以前晓宇出门他会紧张,害怕出事,现在他希望晓宇学着独自面对这个世界,“想出门就一个人出,总要有这个适应过程的。”这天下午,我陪晓宇去附近的银行取钱(他平时花销主要依赖现金)。大多数时候他在自助取款机上就可以解决,但这天他觉得自己时间宽裕,想要到人工柜台办理。我们在沙发区等候叫号,排在前面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。一位穿着西装裤,打着领带,略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突然走过来,跟晓宇打招呼:金老师,我知道你的书!在央视新闻上看见的。他自我介绍是这所银行的行长。晓宇显得手足无措,“我以前姓金,现在不姓金了”,他说给对方听,眼睛却盯着我,像在寻求某种支持。行长显得有点惊讶,一遍遍重复,自己在新闻上看到了他的经历。晓宇站起来,主动和对方握了手,问,您贵姓?对方说了自己的姓氏。哦,X行长,您贵姓?晓宇重复问。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独自生活,“一个人生活那怎么行?孤魂野鬼了就成,吃什么啊?谁给买米啊?病了怎么办?”他说,如果父亲不在了,自己可能会一个人住到精神病院去,没人接是不能出来的,他就要在那里终老了。他说自己现在每天按时服药,让爸爸看着自己吃下去,“他会说乖儿子,好的。”如果要出门,他现在会叫上父亲一起去。出版社发来了新的书稿,他想打印几个章节先看看,让父亲陪自己去小区门口的打印店跑一趟,和高中同学的聚会,他跟父亲说,“你去我才去”。早晨,他在家闷得慌,想出门透透气,叫上父亲一起去坐了76路公交车——这里面有依赖,更重要的是一种隐秘的恐惧:上次在外面发病,已经走了一个了,如果自己在外面再发病,住进精神病院,发生点事情怎么办? 傍晚,晓宇、金性勇和我们几位来访者一起去附近的餐馆吃饭。杭州的冬雨稍停,仍是雾蒙蒙的,浮晃着一层水汽。街道边的腊梅开得正好,树梢上挂了黄色的小灯笼。比起腊梅,金性勇更喜欢樱花,到二月份的时候,运河边的白色樱花就会开了,他以前经常和晓宇去那里散步。没多远我们就走到运河边,桥下面正好有辆白色的载客轮渡驶过。晓宇说他以前坐过,是和公交车差不多的价钱。轮渡顺着河水穿过桥底,将继续往北,一直开,一直开。
-END-